原创螺旋世界里的文明,会探索出怎样的宇宙真理?|科幻小说
时间:2019-11-06 11:58:34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关注微信公众号:不存在科幻(ID:non-exist-SF),回复关键词“创作谈”、“雨果奖”或“长篇”,会有惊喜出现!

本周「不存在科幻」的主题是“另一个世界”。
在今天的故事中,两个异世界的生物为了寻找真相,踏上前往极地的旅途。
看似奇幻的世界,背后却暗藏玄机... ...
有什么话想对不存在科幻说?欢迎来留言~*也可以添加未来局接待员微信:FAA-110,在“不存在科幻”小说讨论群中参与小说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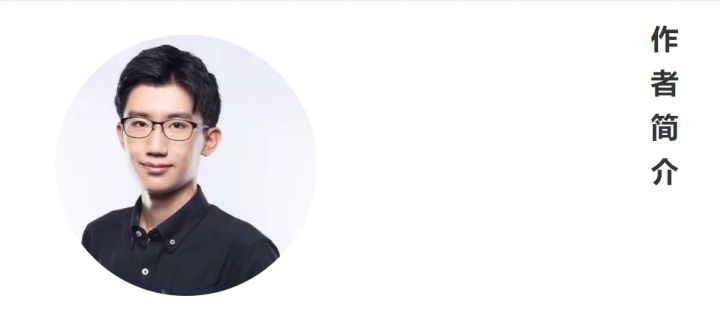
| 王腾 | 未来局签约科幻作家,统计学在读博士。善于构筑具有严谨设计的幻想世界,在探险和游历故事中展现技术美。代表作品《距离的形状》,《夏日往事》。
夏日往事
(全文约20000字,预计阅读时间50分钟)
老者早就注意到了小女孩在不远处注视着自己,但他等了很久才开口
你一定是从极地那边来的观光客吧?我当然能猜得到,冬天已经持续了这么久,现在还能在外面活动的也就只有你们了
这么说你来是想听我讲讲当年的探险?这个我也早就猜到了,现在来找我的孩子们还能有什么别的要求呢?毕竟是个很久远的故事了,那时世界之风都还是相反的方向。嗯,说我拯救了世界可能夸张了点,不管有没有我,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不过,要说我改变了历史,那还有点道理,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我也不怪大家都这么想,毕竟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能讲给你们听了。
其实有很多细节我都没有告诉过别人。但是,你居然能在这里找到我,很奇怪,应该没有人知道我会在这里啊?不管怎么说,这应该算是我们的缘分,那我就全部都告诉你吧。
我年轻的时候正值夏天,强劲的世界之风让整个世界充满了活力,城市和街道可不像现在这么冷清,那时的集市上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卖家的讨价还价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船只在街道和楼宇间来来往往,信差的小艇在大船周围灵活地穿梭,各个城市间的货物,游客,新闻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和效率交流着。那是只有出生在夏天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的世界。有时候中央广场上还会有博览会,你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动植物标本和各种新发明的机器,同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脸上充满着惊异的神情,好奇地浏览每个展品的介绍。真知殿的学者们也时常来到这里致博览会的开幕贺词,同时宣布新的科学发现,有时是游吟歌者来宣读他们新创作的诗篇,无论是谁来,那都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
不过,也只有在停战的间歇才是如此。
我们和极地人的战争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开始了,我自己曾经就是一艘战舰的舰长。从我记事起,极地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我们发动一场远征,他们的意志很坚定,不消灭我们就绝不停手,所有和谈的计划都失败了,毕竟,极地人的语言和思维,甚至他们的身体构造都和我们有很大区别。不过这也不是所有的原因,因为战争的起因要求我们也必须消灭极地人。所以,总要有一方先被消灭,战争才可能结束。
说到战争的起因,你可能不相信,是和我们宇宙学最伟大的发现有关。
你一定知道宇宙稳恒的说法由来已久,我们很早就模糊地知道世间万物在互相转化,守恒于一个不变的总和。宇宙间充满了风,风是世间一切运动的起因,世间也流淌着泉,泉使所有生命和所有机器得以运转。终于有一天,伟大的贤者们证明了风能产生泉,泉也能产生风。这是足以给我们物理学和宇宙学奠基的发现。
这样的评价一点都不夸张,这个发现解释了世界之风如何在我们的心环里感应出源源不断的泉流,赐予我们生命力,我们是如何发出和接收调制信息的风从而彼此交谈,而且还有我们是如何用脊环产生的风和无处不在的世界之风发生作用从而能自由运动。所以宇宙的模型变得十分简洁,泉和风是万物的本源和基本元素,宇宙发生的一切都是这伟大的二元转换的体现。
但是,一位叫静海的学者,却指出我们活着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人疑惑。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世界螺旋里,世界螺旋围成了整个宇宙的边界。世界螺旋里永恒的泉流产生了充满整个宇宙的世界之风——也是世界内部所有泉的来源。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物理学表明,只有变化的风才能在闭合回路里感应生成泉,那么既然我们能从世界之风中获得泉流,就表示世界之风是变化的,进而可以推断世界螺旋里的泉流也在变化,更准确的说,在减弱。
那么,世界螺旋里消失的泉去了哪里?这就是让所有人为之沉默的问题。
其他的学者很快给出了回应,这个现象的解释必然是世界螺旋内部泉流总量的增加,既然宇宙是封闭而且动态平衡的,各种变化和转换永不停息,那么任何此消彼长都必然是暂时的。世间万物的复杂性人们永远无法完全把握,而我们都相信科学的目的之一正是让我们能明白起因和结局而不必追溯每一条具体的变化轨迹。
静海不像其他学者一样止步于这个好听却模糊的回答,她只相信精确的数量,她常常说自己最后的愿望就是弄明白宇宙所守恒的常数究竟是多少。这一次,除非亲眼看到方程平衡,否则她不能允许自己对这个问题盖棺定论。
静海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历史和地理资料,亲自走访了很多地方,包括调查农业生产和居民迁徙记录,她反复的计算最终指向的结果却是这两者远远不相等,世界螺旋内绝大多数消失的泉完全无法解释去向,虽然现在还没有衡量泉流量的统一量度,但即使算上所有误差也差好几个数量级。这个结果可信到足以颠覆她的信念。静海不相信宇宙是漏的,那就恐怕整个宇宙学的基石是错的。
她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宇宙间一定存在某种不可逆的变化,一定有独立于泉与风的第三种元素参与宇宙的演化。衰减的泉与风正是转化成了这种不能再自发逆转的元素。这种元素一定适用一种全新的物理量,尽管现在还没有什么手段能测量和感知它的存在,但她相信世界之泉无法解释的减弱正是这个过程的体现,由此得到了一个时间点,在那一刻之后宇宙间所有的泉与风都变成了那样的元素,而那元素将再也无法发生任何变化,既然宇宙是一个有限封闭系统,那最终一定会达到这样一个死的平衡,而那个时间距今不到五个世代了。
世界很快走向灭亡的结论引起轩然大波,而她近乎幻想的第三元素更是粗暴破坏了当前宇宙学的简洁和对称美。她无法直接证明世界螺旋是否终将干涸,更遑论证明那“不可逆元素”的存在了,但是她预言的事实也似乎无可辩驳。
宇宙是不是真的要陷入永远冻结谁也不知道,但世界之风在逐渐减弱是真的,看来总有一天的确会降到零吧。
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为了在风停之后活的更久,互相掠夺便理所应当了,没人知道战争是怎么爆发的,原本只是和我们剑拔弩张的极地人突然就发动了全面进攻,而我们的舰队也在全力抵挡,有时将反击的前锋推到他们的城市。就这样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我和星蓝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终聚地。
那时我已经离开了舰队,在终聚地找到了一个货运差事。她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那里很少会有人来光顾,终聚地是一个安静而神圣的地方,每个人寿命终止后都会被送到这里,然后离散化,和其他的逝者汇聚一处,无数的颈环,脊环,思想体在这里解离到几乎不能再分割的细小尺度,新生儿就在这里诞生,绝大多数时候,记忆都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损坏,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能对很多自己不曾经历的事情记忆犹新。
一般只有刚成为父母的人才会来到这里,或者是为逝者送行的队伍。她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太像是父母,而最近也没有葬礼要举行。我远远地观察她,只是看到她似乎在寻找什么,不过我没想过要去问问,毕竟再过不久,我连自己现在的工作也不用操心了。
奇怪的是她很快主动找到了我。
那一天我正把最后一批货物搬到船上,眼看着就要迟到了,这时她正好过来搭了把手,时间赶得紧,我们忙碌着各自手头的事情谁都没说话,不过因为有人帮忙,总算是赶上了交接时间,休息的时候,她告诉我自己的名字是星蓝。
“先不要谢我,我是来求你帮忙的,现在只有你能帮我。”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能帮别人忙的人吗?”我说。
“你是船长,我正好需要一位船长”
“曾经是,现在我没有自己的船了,到了明天,连工作用的这艘也要交还了。”
“我听他们说你撞坏了好几次船,因为你...不喜欢穿过隧道?”
我点点头,“确实是这样”。
“你为什么离开舰队?”
“同样的原因,有一次作战,我们在非常密集的建筑群里被敌舰追击,在那样狭窄的地方,我集中不了精神,我手下的船员也就乱作一团,所以被敌舰包围,害我们损失不小。
“为什么?”
“我一直在做同一个噩梦,我梦见自己一个人身处一个非常黑暗幽闭的地方漂流,四周的空间变成实体向我压过来,我始终克服不了这种恐惧,但这不是能保住工作的理由。”
星蓝若有所思,“这是你引路人的记忆吗?”
“我是个无忆者”我摇摇头,“我没有继承谁的记忆,没有引路人,再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我梦见的那种地方…说了这么多你该明白了吧,我帮不了你,我连自己都帮不了。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去港口那边碰碰运气,过几天应该又要开战,城市封锁后,你哪都去不了。哦对了,谢谢你刚才帮忙。”
星蓝没有要走的意思。
“你没听懂吗?”我问。
“我果然没看错,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合适!”星蓝莫名其妙的反应倒是重新引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了!”星蓝说“我有一艘船隐藏在一个地方,现在只需要一个会开船的人。你放心,我不会逼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如果成功,我的船就是你的了,你可以重新做你的船长,而且,那时你就自由了”
星蓝抬手制止了我说话,“你说的对,你确实不像我需要的人选,我之前也找过别人,浪费了很多钱却没有结果,现在我能支付的东西也不多了。”就像是要强调自己的话似的,星蓝从身上摘下来一个精致的饰品,“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是报酬的一部分,现在还值不少钱,到时候,你不仅有船,连经营货运船队的钱也有了。你看怎么样?你要是聪明的话就不会拒绝的。”
那是个表示学者身份的徽印,确实是个很值钱的东西。这么说她是个来自真知殿的学者,也是同样的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那好吧,看来再不领情就有点不识抬举了”我苦笑着点点头。
“这么说你答应了?”星蓝兴奋地跳起来。
“老实说,你看看我现在,这种价码想拒绝也由不得我自己了。我刚才只不过是想试探下你的开价,希望你别介意…”我接过合同,草草看了下就签上了名字“倒是你,你把全部家当赌在我身上,你就这么信任我?”
“和你一样,现在除了这样,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星蓝说“哎等等,我还没告诉你我要去哪.....”
“什么?北极之外?”我感到头晕目眩,“告诉我你是开玩笑。”
“我刚才本打算先说的,不好意思”星蓝无奈地表示歉意,她看起来很真诚的样子让我发不出火,“我们此行是要去考察北极之外一艘探险船的残骸,我必须找到它。这是我唯一的目的。”
“容我提醒你一下,北极是世界螺旋的尽头,小孩子都知道北极圈附近低风的环境就已经会让绝大多数生物遭受冻伤,在北极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生存,更别说有人能航行到那。”
星蓝没有和我争辩,但她的态度一目了然。
“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北极是极地人的地盘,你打算怎么过去?”
“我不知道,但以前曾经有人做到过,或许我们也能。我的开价我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不可能没有危险。”星蓝转身面向我“你曾经是一个军人,你一定记得战争为何爆发,你摧毁过多少艘敌舰?你又在这里日复一日搬运了多少货物?你觉得这些会最后改变什么吗?你为什么要拒绝可能会改变一切的机会呢?极地是世界螺旋的尽头,去过那里的探险船见到过什么,在它上面会不会有阻止世界末日的方法,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吗?”
说真的,虽然我对世界末日不太关心,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想知道,在这个小地方呆了这么久,第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很惊讶自己的回答完全没有犹豫。哦,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船长能反悔已经签好的合同。
我们沉默地看着不远处的保育院,它紧邻着终聚地。护工们耐心教导新生儿改变自己的脊环方向,感受着世界之风,然后驾驭它摇摇晃晃地迈出第一步,另一群幼儿笨拙地调整着颈环的姿态和其中泉流的强弱,产生有韵律的风,艰难地拼出一句完整的话。不远处时间棱锥上的大钟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不知不觉新的一天到来了。日复一日的生活看起来是如此的安宁,足以让人忘记这世上的某处还存在着未知和凶险。
“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你我都知道北极之外是无人能及的死地,如果出了意外,记忆就再也取不回来,你能接受这点吗?”
“我想过很多次了,我不怕真正的死亡。作为学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在时间长河中是多么微不足道,你说我们害怕死后失去意义的亿万世代,又可曾为之前没有自己参与的亿万世代而悲伤呢?”星蓝说,“那你呢?你也不害怕吗?”
“我无所谓,我没什么记忆值得流传下去”我满不在乎地回答。
我一直很好奇星蓝能在什么地方隐藏一整艘船,结果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星蓝带我沿着一条估计只有她知道的密道偷偷来到了索引方碑的里面,索引方碑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它的价值也是可想而知。除了开放参观的时间,这里根本不允许别人随意靠近,但星蓝利用她作为学者的便利,把这里变成了最安全的隐蔽点。
“我们的合同里可不包括一起犯罪。”我抗议道。
“有什么关系?世界可能就要毁灭了,如果我们都死光了,这个方碑要给谁看?而现在,这个象征着我们历史开端的方碑却能帮助我们拯救未来,你不觉得这样让它更有意义了吗?”
她的船就藏在一个挖空的洞里,我必须要先着手进行改造。
目前为止,我们对北极之外唯一的知道的就是那里几乎没有风,所以我们要先准备很多蓄流环,这样能尽可能久地维持生命,另外无风环境中的航行动力需要截然不同的原理,首先我从星蓝给我的零件中组装武器,普通舰炮发射的原理最简单,炮弹和炮座各自带有方向相反的风,松开束缚,强大的斥力就会把炮弹弹射出去,有些舰炮是无后坐力的,因为它也会向反方向发射一枚炮弹,让船的航行不受影响。此外还有结构更复杂威力也更大的轨道加速炮,但我在这里没法制作。
舰炮不仅能用来自卫,在没有风的环境下船要机动,就只能靠舰炮发射的后坐力。此外,我还要制作让船能在坚固物体表面行动的装置,那些东西我起名叫滑轮,滑轮的制作很费功夫。渐渐地星蓝也开始着急了,她时不时催促我快些。
“快也没用“,我回答,”要潜入北极现在只有一个途径,过几天在北极圈边界附近有一场会战,那时防守相对空虚,我们就贴着世界螺旋内壁悄悄越过防线,这是唯一的可行的办法。”
休息的时候,我也会被索引方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画所吸引,那些古老的文字我看不懂,但星蓝应该能解释给我听。
“这是一组名为《造物律》的诗集,是我们的创世神话,它描述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宇宙,居住其中的缓行者一族创造了我们的宇宙万物。”星蓝说,“只不过,关于那些创世者的本尊却众说纷纭,这里面的有些诗篇说他们没有实体,缓行者能驾驭泉和风的力量实现无数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泉与风的灵态化身,而另一些诗篇则暗示缓行者的生命不需要泉和风,他们自有无穷无尽的生命之源。”
不过缓行者的形象在这些古老的壁画里看起来都一样。星蓝指给我看,在每一幅画中他们都像立柱一样直立在固定的接触面上,他们的躯干对称分布着四个条状外延和一个顶端的圆形突出。缓行者本身的形态上中完全看不出任何用来移动和交流的器官,即使所有这些零散的描述全都有真实历史的影子,缓行者也一定是与我们截然不同,完全无法理解的生命形式,从任何角度看他们和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先民或许见过些我们无法想象的事物,但在他们眼中,万物还是神秘与混沌的组合,神话中并没有关于世界最初状态的记载,看来要想弄清消失的世界之泉去往何处,唯一办法就是沿着它的路径走下去,就像那艘传说中的探险船一样。
我很想知道星蓝给我的这么多零件来自哪里,得到的回答是,这些零件,这艘船,是好几代人在这里慢慢累积起来的,星蓝的所有一代代引路人,都为了这同一个目标。
这让我更好奇是为什么。
“静海就是我最早的引路人”星蓝想了很久,终于告诉了我,“终其一生,静海都觉得是她的发现让整个世界陷入战争,而学者的信条使她不能对事实和证据视而不见,她的爱人远光船长是一位探险家,他不辞而别前往北极,追寻世界之泉流去的方向,他相信他的发现能够挽救这个世界,包括他的爱人,但他就此一去不回。现在我很确信他成功离开了北极,他的下落也一定在北极之外的某处。”
“但那不是你的记忆“,我说”那是命运给你的沉重负担”。
“我继承了她的记忆,也同样继承了她的情感和愿望,命运强加的,和我自己想要的又怎么能分得开呢?我的每一代引路人都想见证这场漫长追寻的完结,和她们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就是最后一个”星蓝说,她的目光与我相对时,我觉得那是盛满无数故事的深井,那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体验 。
“你也觉得是因为新发现导致了战争吗?”在临走之前,星蓝问我。
“或许把结论直接归因给未知的新事物不合适的“,我想了想说“未知令人恐惧,让人不知所措,有些事是不能只靠想的。”
“远光船长曾经对我…我的引路人说过,人们用两种方式关心这个世界,一种用头脑将万物抽离成精简的模型,用思想描绘从未见过的事物,另一种则要面对危险,但回报是能亲自看到世界用简单的规则创造出的无限种奇迹,或许他是对的,你也是对的,想知道北极之外有什么,我们去那里看一看不就可以了吗?”
我又想起了那个熟悉的噩梦,整个世界向我坍缩,向我挤压过来,前面只有一条道路,但那不是出口,它通向的是永恒的冻结。
“其实,我也不确定有些事是不是应该被知道”我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一切准备妥当,我们的船沿着世界螺旋的中轴线驶向北极,随着离城市越来越远,掠过我们身边的建筑和渡船也越来越稀疏,这里向所有方向看去都是一望无际,有时候让我有种置身于无限大空间的错觉,似乎在这个空间中没有中心,或者说每一点都是中心,没有参照物让我判断自己是运动还是静止。星蓝说她的名字也是取自《造物律》中的诗篇,据说造物主的世界里有被称为“星空”的概念,那或许真的是同样的感觉。
城市,街道,乡村,森林,荒漠,即使是世界上最寂静的地方也没有完全失去活力,我们看到运输队跨越荒漠来往于每个城市之间。信差们骑着速度最快的天威隼一闪而过,它们强大的爆发力让所到之处裹挟着一阵令人眩晕的强风,一瞬间就越过了视线之外,我至今都没有能看清过一只成年天威隼的样子。他们传递着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收集着游吟歌者们最新的诗歌,核对着每个时区的标准时间。路上星蓝还遇到了她的博物学家朋友,他们遥远地互相问候,他们要去南极观察半个世代才会遇到一次的现象,深潜鲸的幼体从极地之外鲸落墓地的洄游。生物学家们一直想要记录这些孤独的庞然大物完整的生命周期,它们耗尽维持生命的最后力量前往极地以外没有风的死地,在那里分解,诞生的一群群后代在世界之风微弱牵引下回归,开始新一轮回的生命旅程。
而在更远的地方,双方的舰队已经开始零星地集结了,一场新的战役马上就要在那里爆发,按照先前的计划,我们改变方向,离开中轴线,向着世界螺旋的内壁驶去。
对于像我这样一直生活在中轴线附近城市里的人,第一次如此近的打量世界的边缘还是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我眼中,世界的内壁就是无穷尽的巨柱紧密排列组成的巨墙,人间的一切造物都在它的面前显得无比渺小,实在难以想象究竟人们要怎样做,才能发现这些巨柱实际上是围成整个世界的一圈圈螺线?
“很简单,沿着它一直走下去就可以了啊。”星蓝说“当年靠近世界内壁的居民的想法和是你一样的,直到一位游民族长发现这些巨柱有微弱的曲率,族长每次途径临近的村落都会测量,而测量曲率也完全相同,所以他推断这些巨柱实际上是封闭的圆环。如果他沿着其中一个巨柱航行,最后就一定能回到原点。他出发去验证自己的假设,过了很久,久到连他出发的村庄都早已消失以后,他真的回来了。却发现自己身处和出发点相邻的巨柱,他很快想明白了,世界的内壁不是紧密排列的圆环,而是相连的螺线。于是世界螺旋就这样命名了。我们从此知道了世界的形状。”
“所以,思想比世界更大”我感慨道。
“我们不会输给古人的”星蓝回答
我们贴着世界内壁航行,从密集的建筑和植物中穿过,头顶上双方舰队的战斗虽然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但时不时从我们身边掠过的船体碎片和流弹证明了它的激烈程度。不久之后,我们就越过了极地人的防线,北极与众不同的风景也展现在我们眼前。
寻常的植物群落渐渐稀疏了下去。极地人的村落开始零散地分布在广阔的空间中,极地人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身体条件使他们习惯在北极低风的环境中生活。再往前,就是一片当地植物构成的广阔原野。
星蓝说这种叫风轮花的植物是极地特有的物种。它们圆环状的花盘高高立起,畅饮着世界之风带来的泉流。风轮花的生长情况看起来非常整齐。不同大小的风轮花呈现了非常明显的梯次分布,按照星蓝的解释,风轮花的大小和年龄成正比。那这是否就意味着,整个风轮花种群都有着精确的繁殖间隔?风轮花寿命极长,即使最年轻一代的年龄也超过了我们有记载的历史,从没有人见过风轮花的种子萌发。所以这个问题恐怕是只能留给后世的生物学家去解决了。风轮花的种群非常繁茂,几乎填充了所有没有人的空间,它们的梯度在距离遥远的观察者看来几乎是连续的,这至少证明了世界的年龄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知道这个世界等待了多少寂静的时光才产生了智慧和文明的火花,最后有了能理解它本身的造物?
远处突如其来的动静打断了我的思考,有几个物体从极地人的聚落中快速离开,向我们冲了过来。
“是巡逻艇,我们被发现了,不过不要紧,我们离北极圈已经很近了,有机会甩掉他们”我对星蓝说。
“能给他们发信号吗?告诉他们我们没有敌意?”星蓝问
“我们的船上装了这么多武器,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我摇摇头,不过试试也无妨,我向他们发出了信号。
没有反应,对方的船越来越近,它们的细节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他们没发信号,也没回应我们的信号,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说话。准备战斗吧。”我一边说着,一边解除船尾舰炮的保险。
“等一等,现在就用炮弹,过了北极以后怎么办?”
“你看看”我指了指敌舰,“看那些风帆和船体的比例,那是轻型追击炮艇,比我们灵活多了,追上我们只是时间问题,它们的圆盘弹是专门切断风帆回路的,现在不动手的话,难道你想让我们靠惯性飘出北极?”
星蓝没有说话,她不熟练的工程头脑正在努力运转着,权衡着各种选择。不过很快,不远处一组建筑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那是能源中心,由一长列巨大圆环组成,可以从世界之风中获得支持城市运转的泉流。
“就是那里,从那些圆环里穿过去!”
“为什么?我们现在又不是赛艇!”我完全不明白星蓝的用意。
“没时间说了!”星蓝直接登上了驾驶舱,随即船的一个夸张急转弯差点把我从船尾甩出去。
“你在开什么玩笑?”我费力地爬回船舱,把星蓝从驾驶位挤开“真知殿教过你们特技飞行吗?没有的话还是让给我吧!”
“前面那些圆环现在还没接通,待会你要射击前面控制区的杠杆,圆环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一个接一个地闭合,这样就能甩掉他们了。只有一次机会,就看你的了。”星蓝说。
星蓝坚定的神情并没有化解我的疑惑,但是我没有选择,毕竟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的船速的很快,我集中了最大的注意力,直到周围一切慢了下来,我不需要计算提前量,前半生作为军人的经验会指引我射中目标。就这样,圆环在我们身后开始闭合,时间恰好是我们穿过它之后不久。
一开始感觉不到,但穿过八九个圆环之后,敌舰果然被甩得越来越远。当然也有一些想要从圆环外面绕过来,但增加的额外路程也同样让他们落后了很多距离。
我很快想明白了,所有的船帆都带有风,同样会在穿过的圆环里感应产生泉,只是这样船的动能就被转换成了泉的流动,船自然就慢了下来,原来如此,我想起来了过去有些快速赛艇也会用类似的办法实现紧急制动,现在终于明白这个奇特而有效的战术究竟是为什么了。【1】
“看到了吧,不是所有的麻烦都要靠你的技术解决”星蓝看了看后面,然后得意地对我炫耀。
就在这时一发炮弹从我们头顶擦过,紧接着又是一发击中了船体,我赶紧奔到船尾查看情况,竟然还是有一艘敌舰追了上来。看来他们看穿了这个策略,它切断了船帆,采取危险的无风机动,真是做出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拦住我们的姿态。
可是无风机动的船敏捷度明显下降,我抓住时机用船尾炮击中了最后一个圆环,圆环的大块碎片挡住了它的去路,此时它已来不及躲避,在与碎片的不断撞击中完全停止了前进。
“这种麻烦,还是得靠我的技术解决”我对惊魂未定的星蓝说
我们都笑着长松了一口气。
“看,北极圈就要到了!”星蓝说
不用看周围,我也知道我们接近了北极的边界,虽说过程非常的缓慢,但自己的思维真的变得迟钝了,周围的一切看起来变快了不少,身体也没有过去灵活了。尽管如此,前方的景象仍然令我震撼到忘记了自己的小小的不适。
我看到了世界螺旋的内壁,是在每个角度都能看到!世界的直径在这里变小了。前面还会变得更小,在更遥远的前方,世界螺旋的螺线收成了一条中空的通道,这条通道似乎是要通往无限远的地方。
我很难向你形容那种感觉,那就像是整个宇宙渐渐压缩到了你抬头就能把握的尺度,尽管前后两个方向的空间都看不到头。我知道我们正身处世界的动脉,赐予整个宇宙生命的世界之泉在我们四周流过,而我们却对此毫无感觉,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证明我们正身处一股无比强大洪流的中心。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打量构成世界边缘的材料,很光滑,和构成我们自己的物质一样。除了后面可视的一切渐行渐远,再也没有任何参照能标志我们的船还在前进。
只有时间证明着旅行的继续,后面的景物渐渐遥远得失去了细节,变成了和前方一样的令人丧失一切信心的空洞。通道越来越窄,我感到了熟悉的恐怖而致命的压迫感,与先前身处无限空间的感觉完全相反,我觉得自己周围填充了无穷多的物质,而我自己身处空间的最后一丝狭缝中,随时都会被挤压到无限小。这里的景象,这种感觉,和困扰我多年的噩梦,完美地重合在了一起。
我之前真的来过这里。
但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线索,它就像是记忆之海里绝无仅有的一滴,我竭尽全力还是一无所获,终于,稀薄的风让我无法继续思考,但是恐惧却如同一块去不掉的背景,我的全身制不住地颤抖,船也不安地摇晃了起来。
“没事的,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星蓝对我说。她按住了我控制方向的手,力量微弱却坚定。船渐渐稳定了下来,就像我的恐惧也同时在渐渐消退。
毕竟在那个噩梦中,我只是孤身一人。
这次旅行的长度要比我们估计的长很多,已经要开始消耗返程的储备了,而前后望去都仍然是没有区别的深不见底。我的全身都已绷紧,一旦储备减少到危险程度,我就立刻向前发射所有炮弹迅速返航,尽管我们可能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但数字是不会同情我们的,无论什么选择也总比在这北极之外冻死要好。
就在这时,一个物体渐渐从前方黑暗中浮现,挡在了前面的去路上,一艘船的残骸!那不是极地人的船,竟然真的在那里!它孤独地飘浮着,仿佛时时在否认自己是周围虚空的一部分。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艘船并没有完全死去,测风仪告诉我们它的引擎中还有泉的流动。在它航行的时代,将引擎中的泉灌注给人的技术还没有出现,但现在,这些泉足够支持我们登船作进一步研究。
似乎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都想象过自己会在船上看到什么,也许是冻结成雕塑的船员,还保持着生前的动作,也许是最后一个幸存者躲在里面,等着我们去唤醒,这只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它已经沉睡了好几个世代。
事实是,船上一无所有,没有人,没有物品,什么都没有。仿佛这艘船是凭空出现在这里,在它身上不曾发生过任何故事。
星蓝把船里里外外搜索了三遍,然后默默地回到了我身边,我从没有看到过她这样沮丧的样子,明明这是属于几个世代前另一个人的思念。
“星蓝,我很遗憾,但我们得走了”我说
“你不觉得,这艘船是有意布置成这样子吗?”星蓝突然抬起头,没头没脑地说,“这艘船的样子,就好像是有意要告诉别人这里什么也没有...”
“星蓝,我们做不了什么,没人能在这里做什么。”
“...如果他能有办法到这里,那极地人也能,”星蓝没有理我“或许他是为了隐藏什么东西,还要让外人不会起疑心..”
“那好吧,我们再找找”我说,其实我没有指望真的找到什么。
但我作为船长的敏锐观察还是很快发现了异常,我发现了一块排列不正常的装甲板,那是只有熟悉船只结构的人才能发觉的异常,我打开了里面的夹层,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东西
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块谁也没见过的石头,还有一封信。
我们激动地打开了这封沉睡了世代之久的遗书。
亲爱的静海,我真的希望能亲自告诉你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些文字,就表示我的任务已经失败,我再也不能返航,在这里我一无所有,这是我唯一能留下来的东西。
虽然这样说很过分,但请你务必理解我的不辞而别,因为如你所知,极地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处在开战的边缘,与他们的联络是严重的犯罪。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却不能没有他们的帮助。现在我不会要求你原谅我的一意孤行,但我要求你原谅你自己,我一直坚信并不是你的发现让我们的种族自相残杀,因为世界的真相不会偏袒任何人,而且此时此刻,能制止这场悲剧的,如果真的存在,也只能是更多的真相。
距离前人发现世界螺旋的全貌已经过去了四五个世代,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想要去探索世界纵向尽头的人,但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极地之外没有风的环境完全无能为力,南北极一直以来就被视为是宇宙的尽头,在那之外就是拒绝一切生命的死神领域,但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发现能拯救我们的世界,答案必然隐藏在那里。
你无法想象我有多少次想告诉你我所有的计划,想让我们一起沿着世界之泉流去的路线,去见证世界尽头之外的一切,但我知道这次旅程凶多吉少,它的风险只能由像我这样的人来承担。
我们的探险队秘密到达了北极,我已经记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阻碍,稀薄的风让队员们身体虚弱,而当地人的戒备和敌意更像是一堵越不过去的墙,我们用了很久才学会了他们的奇特的语言,努力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然后用我们的知识作为交换,最终,我们的诚意奇迹般地获得了一些极地人的理解,我衷心感谢这些在异国他乡结交的友人,是同样的梦想联结了我们两个世界,而我们共同的努力,一定能把它的边界推向更远的地方。
在新朋友的指点下,极地人社会更加丰富的细节展现无遗,我甚至参观了一艘战舰的建造,缺乏工业技术的他们擅长直接改造自然界的资源。首先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加工风轮花,风轮花圆环状的主干从世界之风中汲取能量,里面充满了循环不息的泉流,极地人把它用作船的风帆和引擎,一个完全长成的风轮花足够为整艘战舰提供动力。
我们一起采集了足够多的风轮花,在北极圈外往返了很多次,我们精心地在路线转折处布置了很多风轮花,它们能产生足够强的风,让我们的船靠近时受到转向的斥力。简单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相当于把导航系统和动力系统都放在了路上而不是船上,所以我们的极地探险船就能前所未有的轻巧。就这样,结合了我们先进的导航理论和极地人精湛的加工技术,我们足以完成前人不曾想象过的壮举。当我们用尽了所有我们能支配的资源以后,在当地人猎户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条正在游向极北之外的深潜鲸,我们把探险船的缆索套在了它的脊背上,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北极之外是无穷无尽的狭窄通道,不管在这里往返多少次,前方那充满无限压迫而又同时无限深远的景象仍然让人从心底战栗不已,最终,深潜鲸耗尽了它的生命之泉,在鲸落墓地死去,那里不断有新的骸骨堆积,又同时被新的一代消耗,所以那里的样子在不同的年代里截然不同,鲸落墓地的存在一直只是个残缺的传说,这一次我们很高兴能亲自了结了这个悬案。
越过了鲸落墓地,我们的船沿着先前布置的路线继续向前,我们经过最后一个中继站后,就只能沿着惯性向前航行,我们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但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远距离了。不知过了多久,大约是越过了半个世界螺旋的距离,终于,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出现在我们眼前。
毫无疑问,这就是世界真正的尽头!它是一堵无限延伸的巨墙,我们向任何方向都看不到它的边界,通道的内壁分化出无数的立柱连接在这面巨墙上,很显然,这表明世界之泉流向了这堵墙的内部。
我们的船无法在这里减速,仍然以惯性向着巨壁前进,很快我们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巨壁上,幸好,船并没有严重受损。
令我们所有人更为吃惊的是,我们看到的巨壁只是薄薄的一层,它也不坚固,刚刚那一下,就已经撞穿了巨壁的表面。
在巨壁的里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宇宙之外的混沌和虚空,恰恰相反,当我们把船拖出来后,发现薄薄的表层内部填充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材料,这种材料从没有人见过,质地十分怪异,似乎暗示了它和这世上所有东西都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这时,从导航员那传来了更让我们惊喜的报告,刚才与巨壁撞击时产生的震波被仪器精确记下了,并且根据收到的回波,这面巨壁的更深处是空的,那里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巨壁的厚度是有限的,可以用震波的数据推算出来,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厚,如果我们能再组织一次同样的远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洞穿那层填充材料,到达巨壁的后面。那里一定有一切的答案。
但是现在我们的补给已经很少了,于是我们只能收集了数据,以及那些材料的样本,踏上了返程。
回到北极营地,我们马上着手准备第二次远征,队员中的学者也开始研究那些来自巨壁内部的材料标本。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令人吃惊的性质,这种材料竟然能完全阻断泉的流动,我们把它命名为绝流岩。
这个世界里的绝大多数物质都不会对泉流造成任何阻碍,少数材料会造成泉的减弱,但除了空间,绝对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泉彻底无法通过。这超出了所有人的常识和想象。不久之后,绝流岩的存在,连同我们远征的秘密暴露了,在极地人眼中,这种能完全阻挡泉流的物质,显然是站在生命的绝对反面。北极圈在极地人的文化中,是生与死的边界线,而我们就这样擅自越过界限,入侵死神的冥府,我们带回的绝流岩,正是最为不祥的预兆。
协助我们的极地人被视为罪不可赦的叛徒,我的队员也遭到了残忍的对待,他们的记忆被彻底抹除,以防止后人知晓这次亵渎的远征。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去,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然而这么多人中,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无辜的,我不仅没有制止战争,反而给了他们更坚定的理由去摧毁我们,我看到了极地人的武装舰队整装待发,我看到了他们的祭师对军队宣布要将我们所有人献祭给死神以求得他对世界的宽恕,我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而且怕是要持续好几个世代,这是对于我,历史上最大的罪人,合情合理的惩罚。
我带着绝流岩以最快的速度驾船冲向北极之外,我用尽了所有的动力,越过了再也无法返航的极限,追击我的舰船一艘艘放弃了追击,我的船慢慢失去了推力,在虚无中漂流,直到我再也感受不到世界之风,很奇怪上一次我到这里时竟然没有注意到这种感觉,它让我想起了一个很少用到的词,那个词应该叫做宁静,无论如何,这里确实是个让我满意的葬身之处。
我无法返回终聚地,我的记忆将和我的队员们一样,被永远淹没在时光深处,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绝望,我记得哲学家曾经谈论过,我们记忆和情感的遗传是不是代表了我们没有谁会真正的死亡,我并不同意,因为我不是这些记忆也不是这些情感。我是它们创生和组织起来的模式,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注定一去不复返。
现在我必须用这样的办法记下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也不会盲目的乐观,或许需要经过好几个世代,才会有下一位访客到达这里,到时候读到这些文字的,一定是继承你记忆的人吧,要是那样的话,我亲爱的探险者同行,你也一定能明白我的感受,虽然我相信生命只是被生与死括在中间的短暂时光,但它总会留下些什么痕迹能绵延久远,就像你读到这里,虽然我和你的引路人都逝去已久,但我们仍然以这样的缘分相遇了。无论世界是不是将要毁灭,这样的奇迹都会让身处时间长河这一端的我,感到无限的宽慰。
我的生命之泉即将冻结,周围的一切看起来越来越快,或许我是第一个孤独面对死亡的人,但我仍然觉得这样的结局充满了美感,不久之后,深潜鲸会吞噬我的身体,构成我的物质会被同化和吸收,参与新生命的组成,伴随它们一代代的远行,死亡,新生和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将永远进行着我的极地之旅。
再见了,愿我们于存在的边缘之外相会。
远光船长,草就于北极之外
给我永远的爱人
我与星蓝都沉默不语,我们各自淹没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的心结解开了,我想象着远光船长的记忆,越过了几个世代的洗练,历经了数不清生命的循环,最终,这仅存的碎片到达了我出生的终聚地,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冥冥中指引我们相会在这里。曾经的噩梦消失了,在世界之外令人绝望的虚无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厚重的时光也站在了我的身后,恐惧早已远去,我的心中无比平静。
星蓝和我的目光相对了,不需要用语言告诉对方,我们都知道了接下来要做的事。
探险船残骸中的泉流可以给我们的舰炮补充能量,保证我们能继续无风机动,也可以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命,根据那封信附带图表的描述,我们完全可以到达世界真正的尽头,然后用我们剩余的所有炮弹击穿世界巨壁。
我们踏上了旅程,探险船的残骸渐渐的在身后消失不见,它再次归于孤独与沉默,像是一座没有字的纪念碑。
“前面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走过很长的距离后,又一次,我们遇到了不怀好意的接待。
一大群球体密集地漂浮在前面的航路上,当船再靠近时,我们看清楚了它的真面目。
“是浮雷!”我对星蓝喊道,“快把船帆放平,船帆产生的风会把它们吸过来!”
浮雷其实是风轮花的果实,在战争中极地人经常把它们播撒在航道上阻止对方舰队前进,它会爆裂出带有锋利边缘的种子,就算船员幸免于难,与它相撞也将严重降低船的速度。这想必就是极地人阻止外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它们在必经之路上,我们躲不开的”
“没办法了,只能发射船尾炮来进行无风机动了,没事的,我们的船体能顶住几颗浮雷的撞击。”我言不由衷地安慰道。
船与浮雷区越来越近,它们终于展示了自己令人心悸的速度,而我们的无风机动不可避免地让这样已经极度危险的相对速度还要变得更快更致命,尽管我用尽全力让船左右躲避,可是浮雷越来越密集了,它们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时不时有浮雷撞在我们的船上,让整艘船沐浴在利刃的暴雨中。
我们的船经不住更多的考验了,船体几乎要被撕碎,船的速度也大大降低了,最后一大群浮雷马上就撞上来了,情急之下,我把船帆高高立起,船帆产生的风立刻吸引了前面涌来的浮雷,就在它们要撞上的一瞬间,我立刻将船帆整个切断然后抛弃,随即,船帆牵引着浮雷的碎片消失在后面的黑暗之中。
前方的航路又重新空旷了起来,偶尔还会有几颗零星的浮雷向我们冲来,但构不成任何威胁了,如同音乐高潮过后的余响。
“我们成功了!”我忍不住欢呼了起来,我确信最坏的已经过去了,虽然还看不到,但前面不远处就应该是道路的尽头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们的去路了。
“星蓝?”
没有回答,星蓝一反常态地沉默了,我回到船舱里找她,她还在那里,但是一块浮雷的碎片击穿了船舱,切断了她的心环。
“没什么关系..真是的..一生最美好的一天还是给毁了...”星蓝艰难地对我笑着说。
我站在星蓝的身边,却没有任何办法能挽救这一切,这里没有合适的急救设备。我能感受到阵阵风的扰动,我知道当一个回路被切断时,泉会在两端来回流动并不断衰减,这个过程会在周围产生微弱的风变化。这种风的扰动就像时钟一样精确,但这一次,它是生命流逝的倒计时。
时间不多了。
我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剩下的路程也显得无比漫长。不知过了多久,终于,这条感觉几乎无尽的通道走到了终点,眼前豁然开朗。在这个时刻,我才完全体会到世界尽头这个词应有的感觉。
无比宏伟的巨壁出现在我们面前,它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平面,没有任何曲率,我们往向任何方向看去,都只看到无限的深远。巨壁的边界,如果真的有的话,也一定遥不可及。我们来时的通道也如远光船长的记载一样,内壁分化出无数立柱与巨壁连接。世界之泉就这样流进巨壁,我再次试着向最远处看去,我们现在的观测技术比那个时代要强不少,虽然不能直接看到,但仍然可以判断巨壁并不是真的无限大,但显然我们不可能去探索它的边界了。
巨壁无比的宏伟和简洁让我们失去了速度的参照,也让我们在震撼中忘记了自己仍然以高速向巨壁冲去。
“看那边,快往那里去,我们就要错过了!”星蓝指着一个方向说。
我把目光投向了星蓝说的方向,那里有一个斑点,是简洁的巨壁上一块无比醒目的异物,它在渐渐地扩大。我马上明白了,那就是之前探险船撞击点。
做最后选择的时刻到了,如果我们现在返回,可能还来得及,但如果我们把最后的资源用于击穿巨壁,我们将只能选择前进,巨壁后面是什么,我们的命运会如何,谁也不知道。
我用目光询问星蓝,星蓝已经说话已经很艰难了,她只是向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把船头校准到了撞击坑的方向,然后发射无后坐力炮,一枚接一枚的炮弹击中巨壁的内层,撞击坑越来越深。但是先前躲避浮雷时消耗了太多的储备,现在我们的炮弹所剩无几。而巨壁还是没有击穿。
如果关于巨壁厚度推算的记载是正确的,那再差一点就能击穿了,但万一记载是错的呢?要是我们所有的努力,根本就只是在巨壁表面戳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瑕疵呢?
但我没有时间怀疑,也没有时间恐惧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孤注一掷。
我把所有的炮弹装在了船尾舰炮上,将它们全部向后发射出去。
巨大的反冲力让船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巨壁上的撞击点以爆炸似的速度在扩大,向我们猛扑过来。
我把自己和星蓝固定在了船的底舱,等待即将到来的撞击。
一瞬间,狂暴的冲击波传遍了我们全身,船舱中细碎的小东西向前猛地飞了出去,船身剧烈地颤抖着,似乎下一秒就要散架。
终于,一切恢复了平静
我解开了固定装置,回到了甲板上。眼前是一片空旷,巨壁在我们的身后。撞击坑也在我们的身后。
和刚才的景象看起来完全一样
“我们是被弹回来了吗?”星蓝问
“不,我们已经穿过了巨壁”,我指了指身后的撞击坑,那已经是一条打通的隧洞。很显然,我们已经到达了巨壁的另一边
所以巨壁的两面是完全对称的。
也就是说巨壁分为了三层,奇异的绝流岩层被夹在了中间。巨壁的两端构造完全一样,包括那无数的立柱,在远处的前方,收成一条细细的通道。
前面那条通道通向哪里呢?是另一个世界螺旋吗?我不相信,最合理的答案应该是最简单的答案,我想那条通道的尽头,就是世界螺旋的南极。
但是,眼前的现实还是要颠覆我们对物理学最基础的认识,整个世界并非是一个联通的回路,但却可以让泉在如此长久的时间中单向流动,就像是泉流进了巨壁,却不再出来。 星蓝想要说什么,她指了指自己破碎的心,我又重新注意到从星蓝断裂的心环那传来的有着固定间隔的脉动。
有着固定间隔...
这个过程不是无限快的,那么如果这个间隔能够进一步拉长呢?如果放大到世界的尺度呢?我不知道巨壁为什么要造成这个样子,绝流岩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们完全可以让思维跳跃一下,我想这就是一种特定的构造,能将泉保存起来的构造!而且,还让泉与风的转化封闭,不会向外衰减,这显然也是可能的。
没错!这才是世界今后的命运,不断减弱的世界之泉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耗散。世界螺旋本身的风在减弱,而相应的结果是世界巨壁存储的泉在增加,但巨壁一定是有限的,所以也不可能容纳无限量的泉,终会有一天,当巨壁蓄满之后,世界之泉会倒流,重新在世界螺旋中产生反向的世界之风,此消彼长,永无止境。至于那预言之中的世界末日,我相信那正是巨壁蓄满的时刻。现在,我们可以断言在那之后世界之泉还会回归,风也会重新充满宇宙,所有的生命还将继续。
所以,宇宙的模型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趋向零的,而是在振荡的周期变化中永不收敛,我们的生命需要宇宙的变化而存续,而宇宙又不可能朝一个方向永远变化下去,一个永生的宇宙,只能是振荡的!宇宙在振荡中永远保持着活力,而我们也能度过风停的时刻,继续历史新的一页。
“星蓝,我们的世界不会毁灭!我们能活下去了!”
“真不错,我也不是很想死哪..”星蓝自嘲地回答
“星蓝...”
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从心底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星蓝都绝对不可能坚持到我们到达南极。
但人总是喜欢用不切实际的愿望说服自己。
“把我留在这里吧”星蓝把学者徽印交到我手里“除掉我的质量,你才能到达南极,这个是应该给你的报酬,拿着这个去真知殿,他们就会让你发言,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不用我说服你,你都明白的,你必须赶到。再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欠你的不是吗。”
“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我一把推开了星蓝给我的东西,“我不是远光,你也不是静海,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应该创造另一种结局…”
“确实不一样啊”星蓝说的话已经开始越来越慢“我们还没扯平,你看,我可没有不辞而别啊。”
来自星蓝心环的脉动渐渐衰弱了下去,里面的生命之泉完全干涸了,我有一种冲动,想要把星蓝带回去,把破碎的心环接好,让生命之泉再注入星蓝体内,然后星蓝就会慢慢醒来,懒洋洋地问我自己睡了多久。
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
生命不能逆转,即使整个世界都能获得新生。
“…星蓝,谢谢你”
我目送星蓝在世界巨壁宏大的背景中渐渐消失不见,然后,我奔向了眼前的黑暗。
黑暗再次吞噬了我,我抛弃了所有能抛弃的一切,然而最后的储备还是要耗尽了,我的船完全失去了一切动力,不断在通道的内壁上撞来撞去,我的思维开始模糊,最后只留下一个简单的冲动,那不是求生的冲动,我感觉累极了,我想就这样冻结在这里。乐观点想,也许不久之后的探险船就能很容易往返于极地之外,那就让他们来取走我的记忆吧,我亲眼见证了世界的尽头,我知晓了宇宙未来的命运,在我孤独而空虚的生活最后,却拥有一段短暂而精彩的相伴时光,在离开时,我是一个付出爱也得到了爱的人,这一路的喜悦和悲伤会在后人的心灵中再次回响,当他们为我默哀时,也会知道,我度过了世上最为幸福的一生。
“对不起了,各位”我终于放开了船的驾驶位。
就在这时,数不清的深潜鲸幼体从我身后狭窄而深远的虚空中浮现,在世界之风遥远而微弱的牵引下它们还是汇聚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涌流,而我的船也在它们构成的汹涌的浪涛重新获得了前进的速度。我并不是宿命论的崇拜者,但也许吧,就连死神也不忍心让我在这旅程的结局到来时放弃。
我的船就这样从南极圈之外回到了世界螺旋,坠毁在南极的荒原上,我失去了意识,直到在南极附近旅行的商队发现了我,把我救回。
后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尽管消除世上的短视,愚昧和隔阂还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你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很有耐心,因为它并不在意我们对它的想法,也可以说世界没有耐心,因为它变化的脚步也不会等待我们。理智最终还是压倒了敌意,和平很快恢复了,因为在世界之泉倒流之后,风的强度又会渐渐重返顶峰,那时风的变化率接近零的冬季也注定会来临,在冬季中我们无法从世界之风中获得能量,我们的后代不能独自撑过冬季,那需要我们整个种族共同的努力。
毕竟现在我们知道了,冬季只是一个季节,还是会等来万物复苏的时候。
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讲这段历史了。
也许这是作为一个无忆者的补偿,老者也没想到过自己能活过好几个世代的时间,一直到冬季的到来。离冬至还有近一个世代,老者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下一个夏天,但时不时能找到他的访客还是会给他独处的生活带来不少久违的生气,老者目送着沿途驻足的一个个听众离开,学者,游吟歌者,信使……而这个故事也将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传递下去。等最后一位听众离开后,老者迟缓地回去整理自己当年远征的图表和标本。他无言地注视着自己的老探险船,他就要离开这里了,在所剩不多的余生里或许永远不会再见。它见证了自己最值得回忆的日子,他无法用一个形容词来概括这一切带给他的回忆。或许美好的人生也是如同宇宙一样,是在振荡中体现活力的吧。在这个年纪,他已经很少思考未来,不过他也有时会想想,后人将会以怎样的感情来装饰这一段记忆呢?人群聚集时嘈杂的风此时已经平息,只留下世界之风似乎仍然永恒的背景。
但他片刻的平静还是被打断了,一个清晰的波动传了过来,在空无一人的大厅无比明显。
“你真的相信宇宙的命运是那样吗?”最早来的小女孩似乎不愿接受故事的结局。
“为什么不?”老者忍不住仔细打量着头一次遇到的怀疑者。
“在你的故事中,你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普通的蓄流环折断时泉会衰减,同时我们能在周围感到扰动,但是和这个宇宙本身相似的构造就不会产生这个现象。【2】”
真是聪明的孩子
“我只能说,积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数学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原理延展出整个数学体系,但却只能从现实中观察现象的规律然后逐渐回归基本的原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们的宇宙模型不会导致任何衰减,因为之后我们无数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泉与风的本质是什么?描述它们互相转化的具体理论是什么?那是我还无法回答的问题,至于衰减时我们能感觉到的扰动,我猜那应该不是简单的泉,或者风导致的,也许是新的东西,该给它起新的名字了。”
小女孩满意地笑道,“你也终于把原因归为未知的新事物了。”
这句话让老者怔住了,他这时才发觉这些话语的波动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韵律,他仔细感受着由思想本身产生的极为微弱的风变化。那是只有非常了解对方才能够辨别出的模式。他再也没有怀疑了,可还是谨慎地问道:
“你…继承了星蓝的记忆?”
“是的,所以我才知道你一定会在这里。”小女孩说,“不过,你可不要说好久不见啊。”
老者的脸上浮现了一抹微笑,但是无数复杂的情感从他的目光中流出,仿佛那段逝去已久的时光在这一刹那汹涌而过。
“当然了,我很高兴认识你”老者最后点点头说。
小女孩准备离开了,老者却陷入了沉思,那段历史感觉已经恍若隔世,星蓝的生命即将到达尽头的时候,自己告诉了她一个美好的答案,他说服了星蓝关于宇宙的永生。星蓝也满意而平静地离开,但他却为此隐藏了真正的答案。在那之后他一直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安宁,因为哪怕他假装自己最后的醒悟没有发生,他在真相面前主动让步,也是对星蓝的不敬。现在是一个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终于能了结这个遗憾。
“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嗯?”小女孩停在了门口
老者犹豫了很久,最后一字一顿地说
“不,我不相信这个答案,我不相信宇宙的永生。”
老者带小女孩来到了真知殿的深处,在那里,他和星蓝远征北极的探险船,他的地图和手稿已经成为了这里的展品,成为这个世界文明史上最珍贵的纪念。老者在还属于他个人管理的用品中拿出了几个他保存完好的风轮花的标本。
“就在巨壁的秘密揭开的时刻,我很快就猜到了风轮花的生长为何存在固定的梯度。因为风轮花的种子只在宇宙的每次振荡开始,风的强度最大且变化率为零的冬至才会萌发,而后来我知道了它们的生长速度和风的变化率成正比。风轮花已经有很多代了,可见宇宙已经存在了很久,后来我又去过北极很多次,用了不少的时间,精确测量或者平均统计,仔细比较每一代的风轮花,无论如何我都得到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结论,风轮花的生长速度在每次的振荡中都越来越慢。”
“风轮花繁衍的周期从没有过任何变化,换句话说是宇宙振荡的振幅在降低。排除了其他的可能,那就一定存在完全独立于风与泉以外的变量使世界的活力在非常缓慢地流失...我想,恐怕静海最终是对的。”
小女孩没有说话,他仔细品味着这些话的意思,然后询问地看向老者。
“没错,宇宙的结构本身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振荡系统,周而复始直到无穷,但却有一个因素不是振荡循环的,我认为它将终结宇宙的永生。”
“我们”
“是的,我们生命的存在,我们的记忆,思想,我们创造和毁灭的一切,这些都是不能自发逆转的事物,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不能被完美重复的过程。我们既然存在,积累记忆,改变世界,留下赋予时间以意义的轨迹,这一切注定了宇宙不再是完美的振荡循环。静海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真的有种我们还没有感知过的物理量,让那些支持我们思考,运动,记忆的能量完全因为它而耗散,再也不能利用,也许它最终会让宇宙停止振荡,也许,这个规律不仅制约我们,也是所有可能宇宙的规律,无论是单调还是振荡,万事万物最终的结局,都将收敛到最终的平衡。”
“你把这个秘密留给了自己,假装你没有发现,这是为什么?”
“因为生命造成的耗散微不足道,留给我们的时间还足够漫长,离宇宙真正的死寂还有数不清的振荡周期,让我们的文明正常地继续下去吧,总有准备好面对这个事实的那一刻。我仍然常常在想宇宙创生之初的泉从何而来,说不定泉并不是只能靠风的变化来产生,也许我们能找到其他的方法产生泉来维持生命,能做好准备离开这个宇宙,如果创世神话是真的,外面就是《造物律》中那个没有边界的宇宙,我们没准就能找到创造这个世界的缓行者,我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他们在哪里,我们在彼此眼中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怎样寻找他们。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告诉你吧,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什么都有可能。”
老者还有个自己的猜想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缓行者对时间的感知与自己完全不同,说不定宇宙的每次振荡对他们来说不过相当于最小的计时单位,说不定这个宇宙本身也不过是他们手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工具,世间数代人的变迁,只是他们眼中无比短暂的一瞬。
不过他还是一


